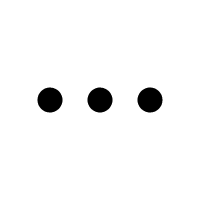中元节,俗称鬼节、施孤、七月半,佛教称为盂兰盆节。

农历七月十五是传统节日 中元节 。中元节本是祭祀 地官 的节日。古人以正月十五为 天官 生日,故定为 上元节 (即 元宵节 ),七月十五为地官生日,故定为中元节,以十月十五为 水官 生日,故定为 下元节 。
到后来,民间又流传七月十五地府开门放鬼魂的传说(部分地方是七月十四,比如广东),于是中元节渐渐具有了 “鬼节” 的意味。又适逢佛教超度亡魂的 “盂兰盆节” 也在这一天,所以七月十五便成了一年之中阴气最重的节日。
在汉魏六朝以前的观念中, “地府” 的所在是 泰山 ,因为泰山府君掌管着人间的生死,而人死后要为泰山府君干活。
《搜神记》 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个叫胡毋班的人走在泰山,突然被一个红衣人带进了泰山府君的宫殿。泰山府君让胡 毋 班给阳间的女婿河伯送信。谁知胡 毋 班死去的老爹见到儿子,也要求他向泰山府君求情免了苦力。泰山府君因胡 毋 班有功,便放了胡 毋 班老爹并让他做土地爷。谁知过了几天胡 毋 班的孩子都死了,原来是胡 毋 班的老爹想念孙子,把他们招到地下。
《搜神记》的时代还没有阎王。而汉末魏晋 佛教 传入中国后,鬼的居所才变成了我们熟悉的 “地狱” 。“地狱”的说法较早见于东汉安世高所译 《十八泥犁经》 ,而我们的 “幽冥界” 的传说,大致是由佛教地狱传说与民间地府传说结合改造的产物。
至于我们熟悉的 酆都城 ,这是由于托名 葛洪 的《枕中书》中认为罗酆山是人死后的聚集地,而后人只是用四川省酆都县来附会这个地方。

中国有着慎终追远,事死如生的传统,“鬼”在中国文化中也意味着逝者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并影响着我们。《韩诗外传》说“鬼者,归也”,《礼记·祭义》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骨肉毙于下,阴为野土。其气发扬于上为昭明。”
在古人眼中,鬼只是生命的回归,回归并不等于终结,而是回到未有生命之前的寂静和暗涌。
其实,我们习惯的说法“阴魂不散”是不正确的,因为古人认为,人的肉身才是阴气的聚集,人的精神却恰恰是阳气的律动,肉身叫“魄”(比如“体魄”一词),精神叫“魂”,魂属阳,魄属阴。灵魂脱离了阴森重浊的臭皮囊(魄),自然变得阳光灿烂,虎虎生风。“阴魂”其实恰恰是“阳魂”。
对死亡的恐惧常常影响了我们对灵魂的看法。但假如我们能正确地认识灵魂的性质,我们也就能正确地认识死亡。有一个故事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道理。
《左传》 里记载,春秋时郑国一度闹鬼,不少人夜间都见到刚去世不久的上卿良霄的鬼魂出现。郑国国君于是请教 子产 ,问世间是否真的有鬼。子产说:
“有。灵魂属阳,魄属阴。属阳的灵魂寄居于属阴的魄中。如果一个人生存条件良好而又有所作为,魂魄就变得强大。所以,即便是布衣蔬食的平民百姓,他们仍然可以变为厉鬼,何况良霄三世公卿,取精用弘(成语“取精用弘”就出自这个故事),他的灵魂显然更加有力量也更加持久。我们看到他的灵魂,又有什么奇怪呢?”
这种“灵魂不死”的观念,古希腊 柏拉图 的 《斐多》 篇也提出了,并且成为了 基督教 灵魂论的先驱,正因为如此,苏格拉底在临刑前慷慨陈词:“我去死,你们去生。哪个更好,只有神知道。”也正因为如此,古罗马大政治家加图读着柏拉图的《斐多》篇,安详地结束了生命。

子产和柏拉图的讲述其实告诉我们,我们不应该只看到灵魂(鬼)的阴森可怖,我们还应该看到灵魂(鬼)的强大,看到生命的生生不息,一阳来复。
笔者认为,古人“天人合一”的内涵,除了哲学老人 汤一介 老先生“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身心之间的和谐”之外,还应该加上人鬼之间的和谐。而人鬼和谐的本质就是人与历史的和谐,是过去与现在的和谐。
虽然 孔子 说“未知生,焉知死。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但孔子并不是认为鬼和死亡就不重要,而是认为在安顿好生命,把握好当下的情况下,讨论死亡和鬼神才有根基。 人是基础,而鬼是超越,生是前提,而死是净化。这就是生死人鬼的辩证关系。
虽然鬼和灵魂是一个庄严的话题,但由于它的神秘性和虚幻性,它也是各种民间故事取之不尽的宝库。可以说,每个中国孩子都是听着老人讲的各种鬼故事长大的。
千百年来,鬼是文学艺术家的“宠儿”,在他们笔下诞生了无数人鬼情未了的旖旎缠绵、夜访吸血鬼的悬疑惊悚,宋定伯捉鬼的壮伟,有钱能使鬼的世故。不管是和谐还是敌意,是喜感还是悲情,这种沟通两界的奇妙景观,不能不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蔚为壮观的民间范式。
这些鬼故事中,鬼的形象各种各样,有的善良,有的凶残,有的搞怪,有的猥琐,而人鬼关系大致可以分为敌对关系、和谐关系和喜剧关系。其实喜剧关系也可以归入和谐关系,而敌对关系也常常以喜剧收场。下面就分享几个有趣的鬼故事。
晋朝时有个 阮瞻 ,不相信有鬼,他有一个著名的推论:“假如人会变成鬼,那人穿的衣服也会变成鬼吗?” 后来有一天晚上,一个“人”找上门来对阮瞻说:“你认为世上没有鬼吗?我就是鬼。”阮瞻吓了一大跳,这一跳可吓得不轻,没过多久阮瞻就被吓死了。
这个故事里,人与鬼当然不算和谐,但也不算对立,因为鬼只是想吓一吓阮瞻,没想到阮瞻自己不争气,哏儿屁了(北方话“死了”),死得既不伟大也不光荣,和生前言之凿凿的气概形成鲜明对比。
与阮瞻类似的一个故事发生在年轻的大学问家 王弼 身上。王弼有一次注解《周易》,参考前人 郑玄 的著作,他说了句“郑玄这个死佬,水平也不过如此吧。”有一天,郑玄的鬼魂找上门来,说:“你小子胆挺肥哈,敢说我的不是?”王弼也吓尿了,没过多久就结束了二十郎当岁的生命。
估计王弼是晚上讲的那句“死佬”,忘了“白天不说人,晚上不说鬼”的古训,结果应验了。所以“晚上不说鬼”的禁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
当然,讲这个故事的人一定是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学者,知道郑玄王弼学术之间的对立,竟至于需要通过鬼现身来解决。
虽然儒家主流思想中鬼是严肃的,是需要“敬而远之”的,但民间文学的鬼却不仅有人的七情六欲,而且还有人的贪婪、猥琐、懒惰等缺点。最典型的要数我们常说的那句话“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句话是对刘义庆 《幽明录》 里一个故事的概括:
有一个新死的鬼十分瘦小,遇到地狱里肥肥胖胖的鬼同伴,很是羡慕,问他如何增肥。胖鬼告诉他:如果到人间吓一吓人,人们就会害怕,就会供奉祭品。你把这些祭品都吃了,就可以像我一样肥了。
于是瘦鬼照着办,他到了一户人家,见家里有一口磨,于是就小跑着推了起来。他想以自己那看不见的身体推磨来显示灵力,逼主人献祭。但恰好这户人家是穷人,没钱买祭品,于是这个可怜的瘦鬼不仅没吃到便宜,还因为推磨而累得更瘦。
在这个故事之前晋朝人鲁褒写过一篇 《钱神论》 ,文章里有一句话叫“有钱能使鬼”,后来跟这个推磨的故事一合成,就变成了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个俗话了。

鬼虽然常常未能免俗,但也常常被人间道德所约束甚至感化。其实鬼也是人变的,鬼与人之间并没有“心灵”的鸿沟。
《幽明录》里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鬼向一个人勒索80两银子,威胁说如果不给钱,老婆就会死,那人偏偏不给,于是老婆死了。鬼又要挟道如果不给钱,儿子就会死,那人仍然不给,于是儿子死了。鬼再次要挟:如果不给钱,你本人就会死。那人还是不给。
鬼被这个人的倔强和骨气折服,于是坦白说:其实你的妻子和儿子都是阳寿已尽,不管给不给钱他们都会死。但你坚决不给钱还是很有种!你是个有福的人,能活到80岁。后来这个人果然天年善终。
其实这个故事很像《左传》里太史四兄弟的故事:齐国崔杼弑君后威逼史官篡改历史,隐匿自己恶行,但史官四兄弟都拒不执行,老大老二老三都被崔杼杀死,老四同样不执行,崔杼无奈,只好放了老四。
鬼和恶人在人的德性面前都不得不收敛和心折,这说明道德的力量正如《诗经》大序里说的一样,是可以“惊天地,动鬼神”的。
也正因为鬼与人的这种异质而同构的特性,所以人们对鬼神也渐渐从害怕到不怕。 “不怕鬼”的思想由来已久。 《庄子·达生》 篇就讲了一个“齐桓公见鬼”的故事。
齐桓公 在沼泽中见到鬼,忙问 管仲 见到什么,管仲说没有。齐桓公受到惊吓,大病不起。有一个叫告敖的人对桓公说:“这是您自己伤害自己。鬼怎么能伤害您呢?如果一个人身上总是散发戾气,那他的精气神就会散,从而产生易怒、健忘和幻觉。积累得久了,就会得病。”
桓公又问世上是否有鬼,告敖说:“有。室内的鬼名叫履,灶房的鬼叫髻。院子里的粪土堆上,有叫雷霆的鬼;在东北方的墙脚下,有倍阿鲑蠪一类的鬼;在西北方的墙脚下,有泆阳鬼;水中的鬼叫罔象,丘陵的鬼叫峷,山上的鬼叫夔,原野上的鬼叫彷徨,而沼泽地里的鬼则叫委蛇。” 告敖又说,见到沼泽中的委蛇,则可以称霸。桓公于是大愈。
这个故事有几点非常有趣:鬼是心造的幻影;鬼并非全部都可怕,有“害鬼”也有“益鬼“;如果到处都有鬼,鬼就不可怕了。
还有一个有趣的不怕鬼的故事。
阮籍 有一次晚上点灯读书,见到了鬼,他连忙一口气把灯吹灭,但他灭灯的原因并不是怕鬼,而是“耻与鬼争光。”在阮籍看来,鬼除了吓人就没有别的本事。因此,对鬼的态度便从战略上蔑视它发展为耻与为伍,进而连秉烛共居都成了污点,竟至于灭之犹恐不及,这恐怕只有魏晋名士才有这种气概。
世纪诗人 聂绀弩 ,在经历了人生和国家的浩劫后,写下了“哀莫大于心不死,名曾羞与鬼争光”的诗句,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当然,人鬼同构的思想,演绎得最多的还是人鬼之间的爱情,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 霍小玉、聂小倩 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千年,家喻户晓,在新时期被搬上电视电影屏幕,更是留下许多经典的银幕形象,以至于大作家 宁财神 这个笔名都要和《聊斋·聂小倩》的男主角宁采臣谐音。
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在这里再讲述就难免陈言务去之讥了。其实这些人鬼恋的故事,体现的与其说是民间对神秘界的猎奇,不如说是对人伦关系的扩充,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对自然秩序的合理想象。
《聊斋》 一书本是“借鬼狐说教”,因为古人向来有“圣人神道设教”的传统。其实记录了《董永卖身葬父》故事的《搜神记》同样也是“借神鬼说教”。须知编《搜神记》的 干宝 并不是蒲松龄式的失意文人,他是东晋史学家和思想家,著有记录晋朝历史的 《晋纪》 和政治哲学论《晋武革命论》。
《搜神记》里记录的许多孝子孝女感动鬼神然后人鬼(神)相恋的故事,还有被录入《二十四孝》的《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的故事,其实也是对晋朝“以孝治天下”政策的一种图解。
这些民间鬼故事经历了精英的整理和升华,它的神秘意味便升华为道德意味,它的鬼神色彩便具备了人的色彩,这也就是儒学大师 冯友兰 先生说的“儒学使宗教变成了诗。”
这个“诗”当然不是诗词歌赋的诗,这个“诗”更像 亚里士多德 所说的“诗表达的是可能发生的事。”这种“可能发生”也即是一种理性的必然,宗教变成“诗”其实就是德国大思想家 马克斯·韦伯 评价中国先秦思想时所说的 “理性化” 。
如果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并且敬鬼神而远之是一种消极的理性化,那么东晋时期把民间鬼神传说改造和吸纳进儒家道德谱系和文化谱系,则是一种积极的理性化,而且这种理性化不露痕迹,炉火纯青,不得不让人对儒学的包容性叹为观止。
那么,在崇尚科学的现代,我们应该如何对待鬼神呢?“敬而远之”和“不怕鬼”,其实都各有道理。
两千年前的荀子,对于祭祀和鬼神这一类看起来可有可无,若有若无的事物有一个经典的论述“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
对于那些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存在,君子将它们理解成一种必要的文化,理解为一种教化民众维护秩序的政治智慧,也理解为人区别于禽兽的高贵性所在,而无知民众则将它理解为真实存在的灵异来迷信,却不懂得真心敬畏、努力修德。
所以笔者以为,对于鬼神的正确态度,敬是必须的,不怕也是必须的,在 “敬而远之” 的基础上还应该 “畏而不怕” ,鬼神固然不可怕,甚至不存在,但我们仍然必须心存敬畏。须知“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倘无敬畏,则无所不为,无所不为则难免无恶不作。
鬼神的意义,一是给我们历史感,让我们不忘先人的遗泽,在追思中自勉、自强,不堕家声,不忝所生,传承高贵,恩泽后世;鬼神的另一种意义就在于给我们敬畏感,让我们约束自己,善待他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这种“人鬼和谐”中开出人与历史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或许是新时代“鬼节”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