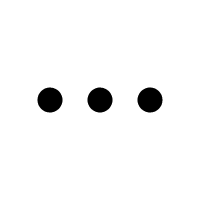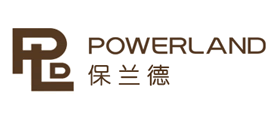《麻雀》讲述的是汪伪政权时期,代号为“麻雀”的共产党员陈深为获得日军“归零”计划,麻雀电视剧大结局是什么?李易峰周冬雨张鲁一张若昀结局揭秘。
电视剧麻雀里李易峰、周冬雨、张鲁一、张若昀、阚清子、尹正、李小冉每个人的结局揭秘。
陈深在谍战剧《麻雀》中是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地下党员,他不仅仅是位中共地下党员,还是汪伪特工总部的一名特工,曾经是一位剃头匠,因为救过毕忠良 的命,因此毕忠良和陈深的关系看似很好,不过,却在一次行动中被毕忠良怀疑陈深的另一个身份,那麻雀中陈深最后的结局如何呢?这部剧的大结局又是什么呢?

三年来,他 以为组织早已将他遗忘,每天混迹在纸醉金迷中,面对敌人不能打不能杀,只能赔笑,这样的生活让陈深痛苦而迷茫,好在,“宰相”终于同他接了头,可惜的是, 没多久“宰相”就暴露了。在非常时期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并受命“转投”汪伪特工机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算是一个混得不错的上海“白相人”,有点 儿职位,能呼风唤雨。但是浮华的背后,他是一名沉默的战士,经历着表面波澜不惊、实则惊心动魄的战斗。
《麻雀》中陈深两重身份曝光!一重是共-产-党的革命者!!另一重是汪伪政府中的一员!!
实际上在小说中陈深是没有死的,虽然在文章的最后陈深开着一辆救护车进了黄浦江,并且在不久之后陈深引爆了相当于自杀式的手雷,他的大哥毕忠良看着水面上的青烟坚定的认为陈深已经死了,但是实际上陈深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至于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没有人知道,因为在不久后的又一次接头任务中有一个男人自称代号是麻雀,在和一个代号叫做布谷鸟的女人说话,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最好的。
这是在小说《麻雀》中的陈深是不是没死这个问题的答案。
电视剧麻雀里陈深徐碧城毕忠良唐山海李小男每个人的结局揭秘
陈深:炸车跳江毁容了,后来多年出现在舞厅,与GD特务接头,被国军的人追捕,跟开头宰相在舞厅被追捕的样子一样,笑对人生,迎面对着追捕过来的特务,开放式结局。
毕忠良:以为陈深被自己杀掉了,愧疚的点了三炷香。随后执行任务被黑化受了很大刺激的徐碧城埋伏炸弹在行驶路线炸死,而且炸弹上有徐碧城特备的毒药,就算真的成功逃了,毒素也会入侵身体,让其慢慢折磨致死。

徐碧城:后期因为唐山海的死受了很大刺激,变得寡言冷漠无情,而且机智。后来因为以为陈深死了,受到的刺激更大了,使得人精神更不稳定。在毕忠良的路线埋伏带有剧毒的炸弹炸死了毕忠良。帮陈深照顾皮皮。后来让陶大春跟随其成为国军大特务,多年后追捕共D特工,在舞厅遇到了毁容的男主,但是不知道男主其实没死,开放式结局。(电视剧好像有被策反成GD,但从片花、官方介绍,以及前期作者埋下的种种伏笔来看,悲剧结局和黑化是不变的)
唐山海:被苏三省几回合端掉了老窝识破了身份,属于自己的战略性失败而暴露,临终悄悄在陈深耳边说叫陈深照顾好徐碧城。被苏三省和其余特务活埋,自己大唱长城谣,活埋致死,头部充满了血液,被苏三省一脚踢爆了脑袋。(电视剧是活埋加铁锹打爆脑袋,更惨了)
李小男:其实真实身份是男主上线特工医生,为人看似活泼,其实心思慎密而聪明,埋伏在男主身边,保护男主安全。(男主原著和电视剧一直不知道,到最后李小男暴露了才恍然大悟)假装喜欢苏三省,勾引苏三省并且假装有胃病获取情报。最后被苏三省识破,苏三省原著就非常变态,以为李小男有胃病还答应一定要治好李小男的胃病,结果知道李小男只是在骗他。因爱生恨而且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电视剧应该会让苏三省更加人性化,单纯的因爱生恨),叫特务塞毛巾进李小男的胃里,要勾出胃获取被吞下的情报纸,挖出李小男的胃致其死亡。

苏三省:心理阴暗极具有野心,业务能力一流,为人心狠手辣,性格扭曲的变态。(原著描写出场被雨淋湿,就像地狱里冒出来的水鬼一样,电视剧出场便也是这样。)嫉妒唐山海的出身和家境(电视剧新增和唐山海有很多对手戏哈,而且据说唐山海48集后才领便当)。深爱李小男(电视剧也新增了和李小男很多感情戏哦,哈哈期待),觉得李小男是自己唯一信任的挚爱。最后知道李小男骗了他,不禁因爱生恨残忍杀害李小男。亲手毁灭了自己灵魂深处唯一的单纯,毁灭了自己的爱情。在追捕男主的过程中,男主给李小男报仇,放到了苏三省,拿着尖刀按着苏三省的肚子胃部,随即陶大春说帮男主报仇,杀害了苏三省。(电视剧是男主杀得)
柳美娜:原著结局最好的一个女子,喜欢男主,帮男主获取了终极计划,男主为了保护柳美娜,帮助柳美娜逃命,柳美娜逃回了乡下,和一个喜欢她的男人结婚了。(但貌似电视剧柳美娜喜欢唐山海,而且好像还有中弹的镜头,估计也是悲剧了)
嫂子(毕忠良老婆):原著就有很重的病,信教,但是最后结局下落不明,貌似没死,但是终日郁郁寡欢,最后陈深嘱咐他人好好照顾他多年未见的嫂子,应该还没死。
(电视剧最后应该是万念俱灰的出家皈依天主教了,因为有修女装扮)
李默群:电视剧虚构人物,为原著两个大BOSS的合体,结局不明,应该也是挂了。

沈秋霞(宰相):原著是男主前妻,开头就在舞厅告诉男主消息,随后被追捕,为了不拖累任何人,饮弹自杀。(原著陈深都30多岁了,电视剧作者说方便剧情流畅,而且不那么复杂,干脆一笔带过改成嫂子。)
【麻雀原著最终章】
【上海往事】
即便是一只蜘蛛,她也会在雨后选择一个角落回忆往事。
现在就是一个雨水充沛的午后,我觉得自己像一株葱茏的中年植物,想要把脚长成根须的模样。我必须老实交待,我生于诸暨县,枫桥镇,丹桂房村,如果你不明白,你就想象一下一座江南的村庄。武侠小说中少年侠客骑着马披着蓑衣,一般都会打马跃过这样雨水不断的村庄。一闪而过啊,一闪而过。我生活在杭州,在城西吃住,在闹市区工作。我总是在微醺的时候迷恋和想象上海,她是我生命中一个时常重复的长梦。如果给这个梦一个时间,我希望她是民国。
民国年间的“孤岛”时期,硝烟还没来得及散尽,沉闷的炮声刚刚过去,但上海的繁华不会输于现在。《色戒》中王佳芝坐着叮叮作响的轨道电车,微雨洒进了车窗,我觉得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镜头。在车墩影视城,我看到一位开这种车的中年男人,他穿着脏兮兮的灰白色制服,面无表情地为一个新开的戏把车子开过来又开过去。我觉得我喜欢这种单调的职业,我愿意当这样一个在电车上发呆的司机,哪怕开的是没有乘客的空车。
在同一条短小的路上,反复地脸含愁容地开着同一辆作为道具的电车,这是一种变相的幸福。

现在,请假定这是一辆空车,车里装满的必定是我民国年间的忧伤。然后,枪声响起来,汪伪、军统特务,日本宪兵和特务机关,共产党地下人员,在这样的一座城市里开始暗战。那种平静之中的惊心动魄,是一种比曲别针还弯曲但却闪亮的人生。2010年的某一天,我开始创作电视剧《旗袍》,一个叫丁默群的清瘦男人,一直都坐在极司菲尔路汪伪特务机关的某张皮沙发上,一坐就坐过去他的一生。我不知道是为王志文而写了一个丁默群,还是丁默群本来就为几十年后的王志文活过一回。总之《旗袍》就这样粉墨登场,女一号马苏不停地变换着旗袍,在这部剧集里走来走去,仿佛她有用不完的力气似的。
我十分害怕她细小的腰肢,有一天因为高跟鞋的突然折断,而在百乐门舞厅里折了她的腰。
我想我是迷恋旗袍的。我认为专做旗袍的裁缝,一定会有一只藤箱,里面装满了皮尺、剪刀、划粉、布料、盘扣,以及一应俱全的各式工具。他去为太太小姐量体裁衣,民国才会显得丰盈起来。他的藤箱如同我的电脑包,同样是为谋生而使用。我总是背着电脑包风尘仆仆地赶往剧组,在那儿住下来开始我的生活。所有的演员都在演戏,我有时候也去拍摄现场看看,可是我怎么都觉得我一步步走过去,走进的不是片场是我的人生。
《旗袍》是写得很辛苦的一个剧,我留下的纪念不是一袭旗袍,而是拍戏的某个夜晚,我在片场捡起的日本宪兵枪膛中跳出的子弹壳。现在这枚子弹壳躺在我的书房里,见到它时,我总是仿佛能听到一声枪响。多么响亮啊,像一记生活的耳光。
在我十分少年的时候,我认为电视机是一种妖怪。
其实你可以想象的。在上海龙江路75弄12号低矮的房子里,一个少年目光呆板,盯着十二寸的黑白电视机看电视。那时候电视机没有遥控器,换台时需要转动旋扭,旋转的时候啪啪作响。那时候电视机的屏幕是外突的,闪着灰色的光,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乡村孕妇。这个哈着腰长得壮实肉感土里土气的少年,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了盯电视屏幕上。每天晚上,他看电视都要看到半夜,直到屏幕上雪花纷纷扬扬。这让少年想到了故乡枫桥寒冷的冬天,他在上海里弄外婆家狭小得转身都困难的房子里,十分坚定地认为电视机是一个妖怪。如果它不是妖怪,它怎么会把那么多的人间悲欢装进一个小小的匣子里。
少年就是我,那时候的我肯定不是玉树临风,我很肉,长得很像小兵张嘎。
那时候我检阅的电视大部分都只有上下集,你可以想象一下那大概是三十年前。三十年是一个什么概念,三十年就是一个哇哇降生的八零后突然间娶妻生子,这需要多少的光阴啊。接着我看到的是《虾球传》《蛙女》《上海滩》《霍元甲》《陈真》《万水千山总是情》……

许多睡不着的夜晚,我从外婆家打开门溜出去,穿着短裤汗背心趿着拖鞋。我完全地顺着路灯光铺成的马路走,手里捏着一根捡来的短棍。短棍在墙体上行走,划过了高大的围墙,划下一道细碎的白色印痕。我觉得那时候我的少年是如此地充满忧伤,我一个又一个地数着路灯,一直走到离开外婆家很远很远,一直走到摆渡的码头,一直走到天色发白,一直走到可以看到“牡丹牌”电视机的巨大广告。然后我站住了,像一个马路上突兀的标点符号。
我就那么顺着许昌路走,一直走到杨树浦发电厂附近。然后回头的时候选择另一条路,转个弯是怀德路,接着是龙江路。我把这些角角落落都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向延安》中,我小小的胸腔里装满了整个的上海。
那时候我认为上海就是我的。
《代号十三钗》《向延安》《捕风者》《旗袍旗袍》……我笔下的这些小说或者电视剧,一个又一个地把发生地选择在了上海。上海是一个产生故事的地方,当然也产生大量的工人。我喜欢看到的旅行包的图案是工厂正在冒烟,上面有两个字:上海。我的大舅是国棉十三厂的,大舅妈是上海拖拉机厂的。
我的小舅和小舅妈都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的。二阿姨和二姨夫都是上海钢铁二厂的。我的四姨是上海医疗设备器械厂的,四姨夫在一家金店工作。我的小姨和小姨夫是环卫管理处的。我的母亲是老三,她戴着大红花上山下乡,雄赳赳地来到了丹桂房村。她看到了辽阔而贫穷的田野时,她觉得上海反而是她一个刚刚发生过的梦。那时候她十分青春,但是她很快就明白,青春逝去的速度,如同闪电。
这就是普通的上海家庭的成员,他们都是工人。我少年的辰光也希望成为一名工人,我在外婆家的屋子里,能听到不远处“新沪钢铁厂”巨大的机器声。这样的声音像潮水一样,慢慢地淹过来,将我整个的少年都淹没了。我见证了那时候十分年轻的舅舅阿姨们的恋爱,他们的脸上闪动着光洁的笑容。现在我回头想想,他们生活得多么像一部电视剧。
我开始恋爱的时候,女朋友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候我从部队回来没多久,我傻愣愣地坐在她家里。我们有时候谈天很热烈,我们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谈起了文学。我们有时候一言不发,坐成一张照片的样子。我觉得1992年真是一个十分好的年代,我们穷得只剩下大把的时间了。那时候我用28寸的自行车把她驮来驮去,那时候我们的样子简直比风还要嚣张。我穿着旧军装敞着怀,露出雪白的衬衣,她穿着自己做的棉布裙子。我们开始看一部叫《过把瘾》的电视剧,每天都会在午夜播放。我喜欢上王志文的演技,但是我永远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写一个叫《旗袍》的剧本,有一天王志文会来演这部电视剧,有一天会和王志文在横店影视城的一个饭店里喝酒。
妈的!电视真是一个妖怪。
极司菲尔路76号以及上海歹土是我梦里面最深的黑白底片很多次我啃着碎面包,或者吃半碗黄酒,在潦草生活中看《色戒》。我对那些被人津津乐道的镜头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76号这个汪伪特务机关里,电影一开场就出现的那条狼狗。我喜欢那条狼狗的眼神,那是一种电一样的攻击性眼神。我还喜欢那辆黄包车,蹬车的汉子屁股离开座凳,这让我想起我年轻时候的骑车姿势。当然我也喜欢看那辆有轨电车,我觉得我一半的魂一定丢在那辆车上了。用现在的话来说,那辆车可以有另一个名字,叫往事。
也许你已经明白,我把这部电影当作纪录片来看。我总是觉得我前世的所有梦都埋在了旧上海的光影里。我固执地爱着上海,偶尔会梦见外祖父和外祖母,梦见火车,梦见火车里下雪天的爱情。这些碎梦构成了可以拼凑的一个剧情。

我疯狂地钻研着极司菲尔路76号的结构,我发现这里面有刑讯室,有办公室,有机要室,有译电室,有图书馆医院,也有行动大队、警察大队……这多么像是一个十分正规的单位,而这个单位里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易先生在文件上签下了命令,他十分平静地告诉手下,把王佳芝给毙了。
扣动扳机是容易的,听到枪响也是容易的,但是签下这个字不容易。我能想象王佳芝在泛着银辉的月光下,会流下眼泪和干净的鼻涕。她一定在想着,青春和爱情是多么的懵懂啊。
我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屋子是杭州城西的一间叫布鲁克的酒店。酒店的219房十分狭小。这个阴雨连绵的夜晚,我的头发蓬乱眼睛血红,我甚至还喝了三两五年陈的黄酒。我实在搞不懂是我梦见了我的一生,还是我的一生都是在梦中。我想,壁虎也会回忆往事的,这种尾巴很脆的动物,我认为完全可以把它当作宠物来养。我不相信它比那些宠物蜥蜴会逊色多少。我想完全可以在壁虎的身上贴一张小的标签,上面写上:正在回忆,请勿打扰。
所有的电视剧,必定是一些人在集体回忆。
遥远是因为我害怕走近,走近是因为我害怕遥远我认识两位上海导演,他们一位要拍我的《向延安》,一位要拍我的《代号》(龙一老师的小说原著)。很多时候我都想选择一个天气晴好的日子,坐着高铁去上海和他们聊聊剧本。最后我没有成行是因为,我十分害怕我坐在高铁车厢的座位里,一个小时不到列车就把所有的路程全部走完了。而在我少年的辰光里,坐着棚车从绍兴到上海要十一个小时,坐着绿皮火车从诸暨到上海要九个小时。突然间一切都变得那么快,让我来不及做好思想准备,有些措手不及。
我的父母,妹妹,以及一些亲人都生活在上海。我十分害怕和上海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年少轻狂时候唱过的歌,其实还跌落在外滩上。但是我知道上海的一切都变了,当我查到我生活过的龙江路75弄早就成了一片林立的高楼时,我更不愿意站在高楼的面前,像一个失魂落魄的流浪汉。
我相信我更愿意站在那片黑压压的低矮的旧民居前,家家户户都在上演着柴米油盐的电视剧。
我不再去想象上海。只愿意在电视剧里重新构架我梦想中的旧时上海。我喜欢《暗算》里最后一个镜头,年迈的柳云龙白发苍苍,看到有人在拍一个戏,戏里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年轻人正打算去执行任务。他看到的不是电视剧了,看到的是从前。我在写《捕风者》的时候,一开始就写到一个女人来到拥挤的上海,在里弄的一间房里,有人把一只包着白布的骨灰盒扔在了她面前,说这就是卢加南同志……
女人没有哭。她替卢加南同志活了下去,她完成了一项项任务,她在上海的任务,是捕风……
女人叫苏响。她没有哭,而我自己写着写着号啕大哭。我被小说中的人物打动,她和我打招呼,她说我们都寻找过爱情的不是吗?我们都愿意去死的不是吗?于是我想,我们都生活在无尽的忧伤中啊。我和我的夫人正在老去,女儿正在青葱。我觉得我们就像一粒被风吹来吹去的草籽,或者就是风的本身,在春天里徜徉。